民粹忽视了什么:检视疫情纾困福利
【当今特约】
2019冠病疫情是前所未有的供给冲击,并诱发需求冲击。在宏观经济学里,经济变化大致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即供给、需求和金融。
顾名思义,供给冲击主要来源于生产(生产效率、原料和劳动)方面的变化,如1973年的石油危机; 需求冲击源自于需求层面,如经济状况不稳定、在风险管理上趋向保守的风险厌恶; 金融危机源自金融体系,如2008年金融危机源自于金融体系对信贷的放松,进而引发投机行为。
冠病疫情导致必须实行封锁,限制商业活动、实施安全社交等措施加上疫情全球化导致生产层面出现大规模“扰乱”,进一步影响需求层面。
生产层面出现冲击,原料价格高涨,商家必须实行撙节措施(价格转移未必可行,反而会对营收造成伤害),员工被裁、减薪或对经济展望不乐观而改变消费行为等等引发需求冲击,而这需求冲击再影响供给,恶性循环于焉形成。
民粹忽视实际效益
踏入2021年,马来西亚疫情不减反增,封锁措施导致很多人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联邦政府从2020年至2021年6月总计拨出5300亿令吉,为疫情导致的经济状况纾困,其中除了延长偿还贷款措施(loan moratoriums,涉及2100亿令吉)之外,其他较大的拨款都涉及国家的福利体制,如雇员公积金的提款(800亿令吉)、薪资补贴计划(WSP,涉及262亿令吉)、援助金(BPN和BPR,涉及215亿令吉)。
这些纾困措施涵盖贫户家庭,涉及国家福利体制,如雇员公积金局(EPF)、社会保险机构(SOSCO),常因民粹主义煽动而受影响,如政治人物要求公积金提款额提高、援助金金额提高等等;但却忽略措施是否真的有效,如何更有效地达到原本政策目的,有哪个群体被遗忘等。
公积金提款是否可以利惠中低阶层?失业、减薪、被迫放无薪假、退休金、职场保险忽略了哪个群体?援助金以全国统一津贴的方式是否有效帮助各州城镇和乡镇的贫穷阶级?
本文主要以量化的方式探讨马来西亚目前福利体制的问题。福利体制主要以两种方式互补,即政府的支出政策(fiscal policy)和强制储蓄、购买保险,如雇员公积金(EPF) 和失业保险(EIS)。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先从强制储蓄、购买保险出发,探讨雇员公积金和失业保险相关的福利议题,再探讨贫穷与援助金的相关福利议题。
关键词组 1 :雇员公积金、隐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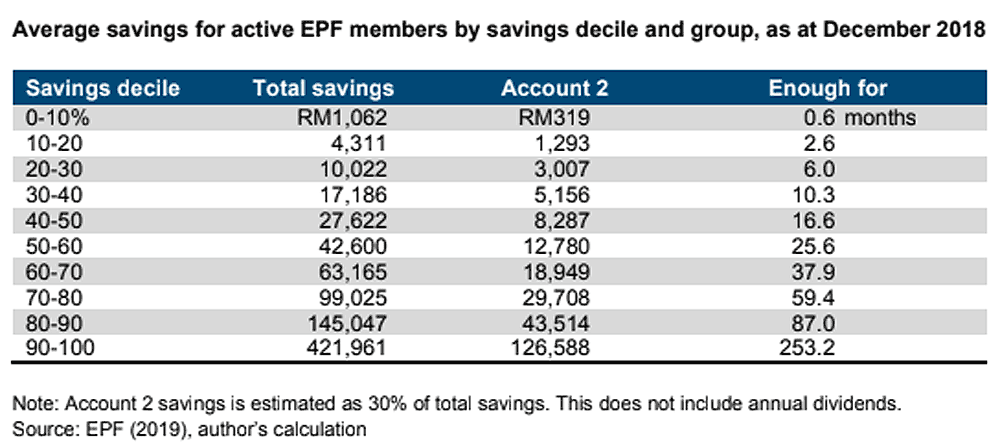
图一:2018年12月,公积金成员的存款额度与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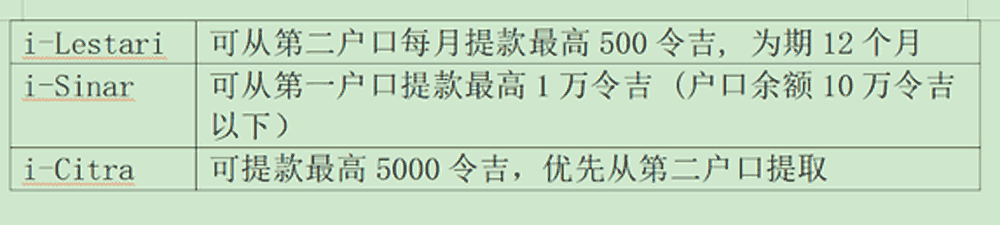
图二:部分各雇员公积金提款详情,资料来自雇员公积金局
从2020年至2021下半年,联邦政府陆续推出i-Lestari、i-Sinar和i-Citra ,让雇员公积金会员提款。根据国库空库智库(Khazanah Research Institute, KRI)的研究,40%雇员公积金活跃会员的第二户口低于6000令吉,根本无法完全受惠于i-Lestari计划 (i-Lestari从第二户口提款,500令吉 x 12个月)。
至于从第一户口提款的i-sinar,储蓄最底30%的活跃会员第一户口甚至没有完全达1万令吉。假设储蓄最低的30%活跃会员都参与 i-Lestari和i-Sinar,他们的公积金存款将耗尽,甚至如果还需要资金周转也无法参与 i-Citra(本文聚焦的是福利政策,因此对象更多的是贫困阶层),耗尽雇员公积金的储蓄也带来退休生活所需费用的机会成本。
同时,国库控股智库的研究也有提到研究的限制,这包括雇员公积金储蓄低也可能是一些刚加入劳动市场的社会新鲜人、也可以是从第二户口提款用以投资在自己(教育)和财富累积上(买房)的青年。
雇员公积金提款的政策也忽略了没有在雇员公积金储蓄的自雇人士和非正式劳动市场的员工。下文会详述自雇人士和非正式劳动市场员工的社会安全网处境。
关键词组 2 :失业保险金、被排除
社会保险机构(Socso)的失业保险系统(Employee Insurance System, EIS)于2018年成立,皆为在私人界工作并缴纳失业保险保费的会员,提供失业津贴。
论广度,社会保险机构在疫情时把社会保险系统的受惠对象从失业人数扩大至被减薪的员工(透过工资补贴计划,PSU)、被迫放无薪假的员工(保留就业计划,ERP)、不符失业保险系统关于合约员工资格的合约员工(透过LOE Assistance for Unqualified CQC and Expiry of FTC计划)。
论深度,薪资5000令吉以上的EIS受保人失业率不亚于薪资1200至1999令吉的失业率,因此把薪资受保额限设定在4000令吉是值得探究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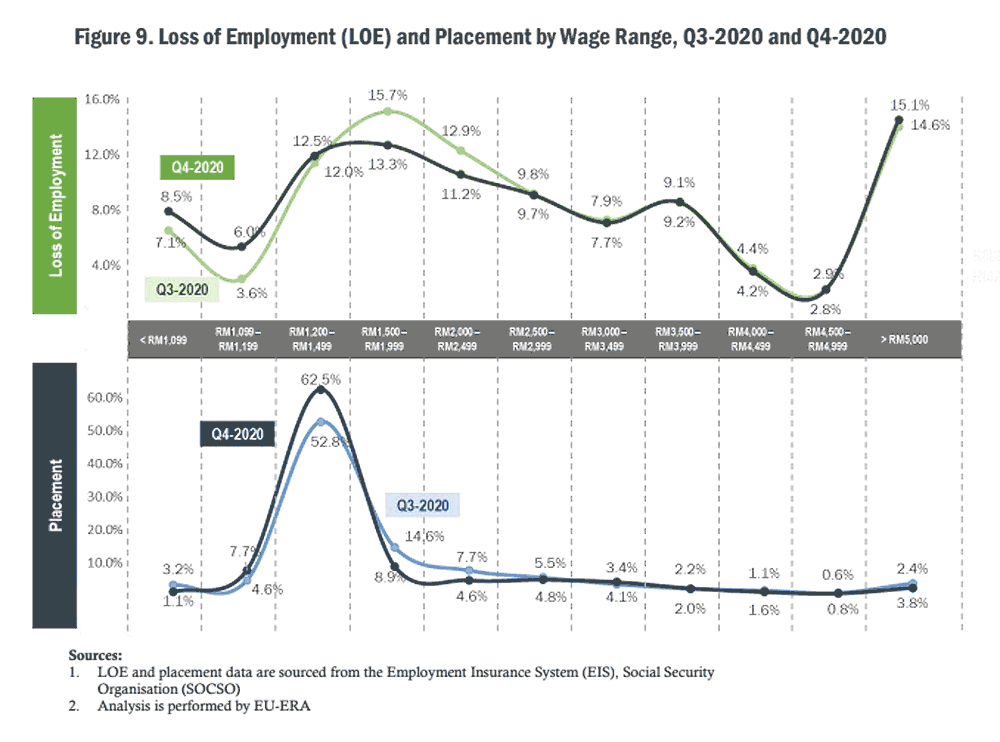
图三(上半个图表):薪资额度与失业比率
失业保险系统让受薪员工受惠,却忽略了非受薪员工。非受薪员工里又分成两种群体,即自雇人士和雇主,两者间的差别在于有没有聘请员工。
福利政策研究较为关注自雇人士,更甚于雇主,毕竟自雇人士的商业规模和收入都比不上雇主,且福利政策是确保人民在面临危机时可以减少冲击。
科技引发共享经济兴起,越来越多人(不分性别、年龄阶层、和城乡)选择成为自雇人士。国库控股智库的研究显示自雇人士从2014年的220万人增长至2019年的270万人(增长50万人)。
该研究也援引统计局(DOSM)民调证实,非受薪员工群体在疫情之下面临比受薪员工群体更大的冲击。在该民调里46.6%的自雇人士和23.8%的雇主表示在疫情时处于失业(受薪阶层只有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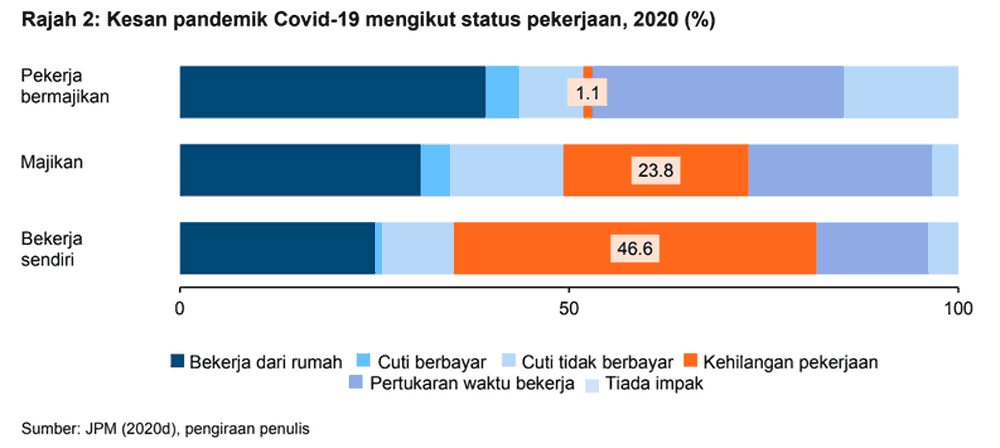
图四:2020年,疫情对受薪职员、业者和自雇人士的影响
目前非受薪员工并不受失业保险系统的保障,自雇人士只获得雇员公积金 i-saraan和社会保险机构的社会安全保险(Skim Keselamatan Sosial Pekerjaan Sendiri)保障。
即便如此,截至2020年6月,仅有26万自雇人士参与雇员公积金的 i-saraan 和3万自雇人士加入社会安全保险。另一边厢,雇主只能通过雇员公积金的自愿缴纳(Caruman Pilihan Sendiri)储蓄退休金。
在劳动市场里还有一个群体几乎在国家福利政策下被遗忘,即非正式员工。非正式员工是那些不受国家福利政策所保障的员工。
在马来西亚的脉络里,非正式员工是那些不被雇员公积金和社会保险机构政策所保障的员工,这群体于2017年占马来西亚劳动市场的39%(560万人),即10人中有4人没有获得雇员公积金和社会保险机构福利政策的援助。
联邦政府在疫情时给部分员工的福利政策是通过公积金(如公积金提款)和社会保险机构发放。如失业保险津贴,以及PRIHATIN之下的津贴延长期限、工资补贴、关怀检验计划/PSP等。
由于非正式员工不被雇员公积金和社会保险机构所保障,因此非正式员工也不能享受这些政策。非正式员工只能享有金钱转移(cash transfer如BPN)类型和普遍型(如电费折扣、免费网络、贷款延期偿还措施等)的援助政策。
约90%的非正式员工属于中低技术员工,伴随较低的薪资水平,在疫情之下他们的处境更险峻。
疫情之下,自雇人士和非正式员工面临失业、减薪和被迫放无薪假都无法获得国家福利体制的保障。
关键词组 3 : 贫穷线边缘群体、有尊严的生活
联邦政府于2019年把原本每户家庭(平均4人)每月980令吉的绝对贫穷线(absolute poverty line)提高至每月2208令吉,2019年马来西亚的贫穷率为5.6%(约40万户家庭)。
如果以相对贫穷线(relative poverty line)计算,马来西亚于2019年拥有17%的家庭(约120万户家庭)处于相对贫穷当中(2936令吉50仙)。
再拿相对贫穷的家庭(120万户)扣除掉贫穷线下的家庭(40万户),即拥有80万户家庭不在贫穷线之内(每月2208令吉),但却在相对贫穷线之内(2936令吉50仙)。
这80万户家庭只要家庭收入减少728令吉50仙就会跌入贫穷线,2020年的贫穷率从2019年5.6%提升至8.4%就印证疫情会使更多家庭掉入贫穷线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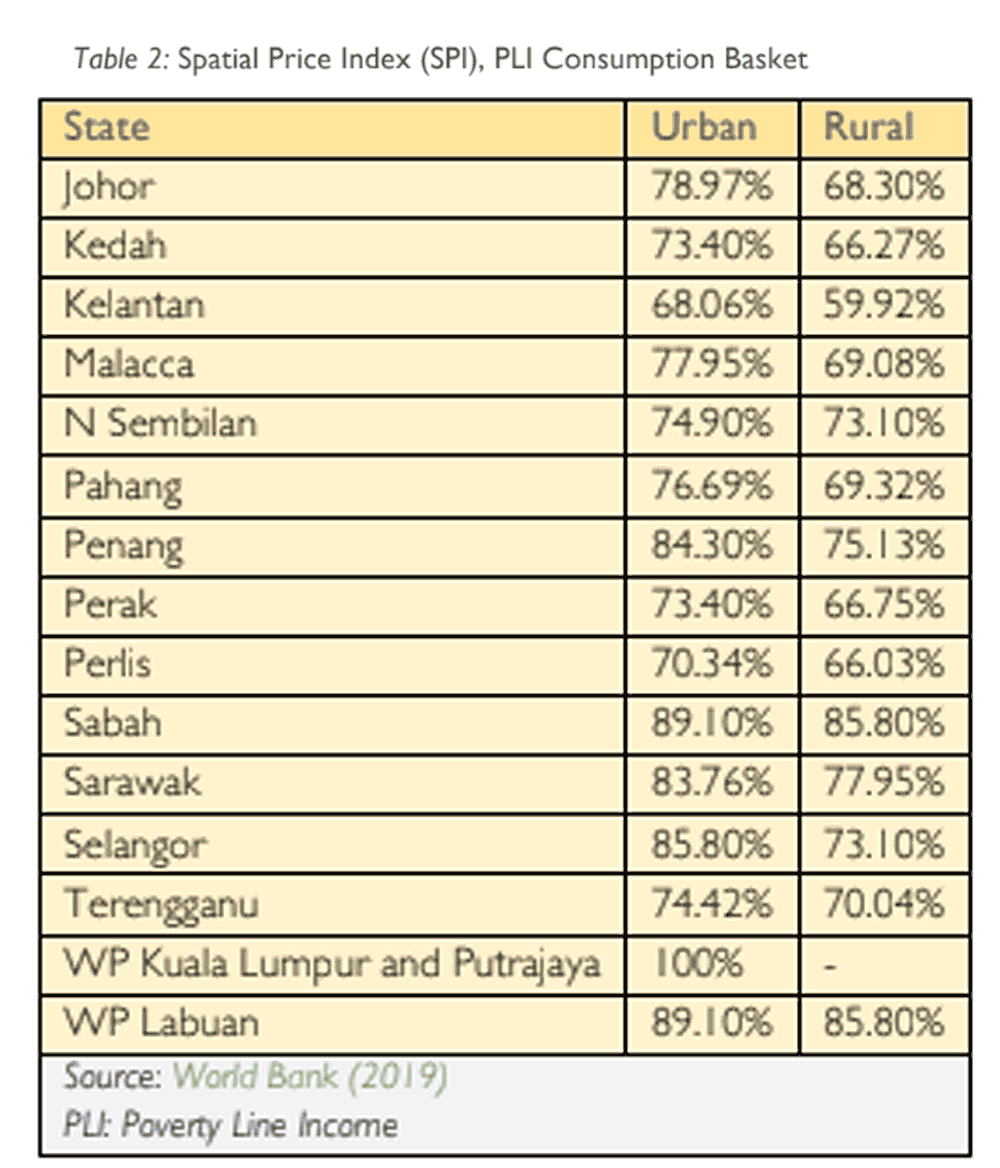
图5:各区域的价格指数
贫户家庭可获得爱民援助金(BPR,之前的BSH/BR1M)的援助,但援助的金额不应该是全国统一的金额,目前爱民援助金的方式忽略了全国各州城乡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异。
根据义腾研究中心(REFSA)的研究(见上图),生活费最高的是吉隆坡和布城(100%),而生活费最低的是吉兰丹乡镇(59.92%),各州的城镇之间和各州的乡镇之间都存在着差距。
除此之外,义腾研究中心也提出生活薪资(living wage)应该免除统一,根据各州城乡的生活水平设立不同的生活薪资,而目前爱民援助金的津贴金额完全不足以补贴贫户家庭收入和生活薪资的差距。
贫穷线的设立确保家庭可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尤其是有能力摄取最基本的营养,而相对贫穷线的设立更多的是数学上的形式(家庭收入中位数乘40至60%)。
在马来西亚的语境里,国家银行于2018年推出生活薪资的概念(雇员公积金也有相应的Belanjawanku),不同于贫穷线,生活薪资估计的是在社会上最低有意义生活水平,准涵盖社交和财务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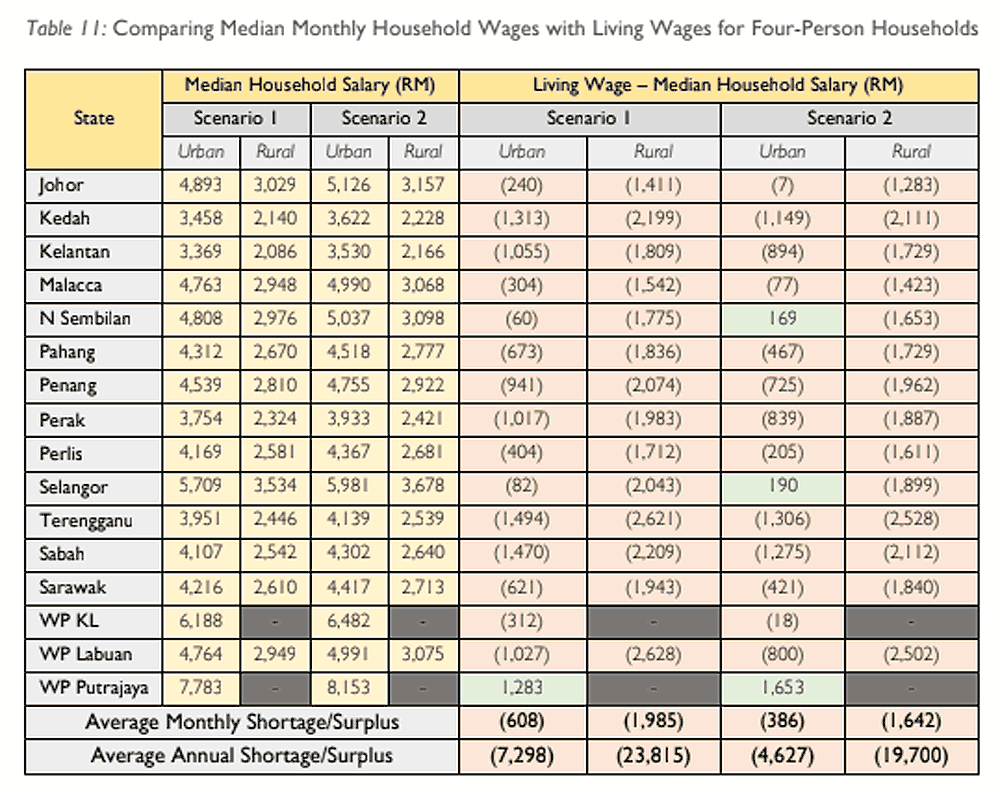
图6: 城镇和乡镇之中,四人家庭的中位数收入对比生活薪资
*Scenario 1 为较悲观的估值,Scenario 2 为较乐观的估值
该研究的作者使用统计局的薪资调查报告(Salaries&Wages Survey Report)预估了一户四人家庭在各别州属里的城镇和乡镇中位数收入在对比生活薪资(国家银行只估值个人、情侣和四人的全国性标准, 作者再延伸对各别州属城镇和乡镇做估值)。
上图显示大部分的家庭中位数收入完全达不到生活薪资水平,除了森美兰城镇、雪兰莪城镇和布城(城镇和乡镇),即便如此也只有布城(城镇和乡镇)的家庭中位数收入大幅度超越生活薪资水平。
同时,乡区家庭中位数收入与理想的生活薪资水平差距甚远,最小的差距即柔佛乡镇也达到每月1283令吉的差距。
城镇的生活费虽然比乡区高,但住在城镇的家庭由于教育水平甚高、从事高技术工作(根据统计局的定义需要大专文凭以上的工作都归类为高技术工作)、双薪家庭而带来更高的家庭收入,因此城镇的家庭即便面临生活费高企比起乡镇家庭更有一定能力对生活费压力做缓冲(offset,见上图)。
生活薪资不只包含最基本的食物(营养)摄取也包含最低限度有意义的生活,如参与社交活动等等。虽然该研究的对比是以中位数和生活薪资做对比,而福利政策针对是贫户家庭(家庭收入中位数以下的家庭),但政府的福利津贴可以以中位数群体与生活薪资的差距做基础。
结语
民间发起举白旗运动、“照顾好彼此”(Kita Jaga Kita)等运动反映了对体制的不信任、失望,体制也仅做出有限的回应。民间、非政府组织、政党纷纷投入救济运动,而政策讨论则多出现在智库。
本文皆以公共政策的研究方式,从冠病疫情的角度出发叙述马来西亚福利体制出现的问题,民间、非政府组织、在野力量可以以此再推进一步做延申讨论,以全国的角度探讨联邦政府层级福利政策的碎片化、财务限制、政治阻力及兼顾理想与务实的福利政策等等,从上至下推动体制改革。
唯有良好的体制和福利政策,才能在社会上论广度、深度、可持续性覆盖更大的社会安全网。
陈明忠,马来亚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数据科学硕士生。即便处于政治狂热与后真相时代,依然深信理性、政策和体制改革的重要。
数据来源
马来西亚统计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DOSM)
社会保险机构(Social Security Organization, SOSCO)
国库控股智库(Khazanah Research Institue, KRI)
义腾研究中心 (Research for Social Advancement, REFSA)
文献目录(bibliography)
Darshan, J. (2020).Uncovering the Plight of Low-Income Malaysia.
Firouz, A. (2020). Why i-Lestari will miss the most vulnerable during Covid-19 (Issue March).
Firouz, A., & Hamid, H. A. (2021). Lebih Sejuta Isi Rumah Miskin Jika Tiada Bantuan Sepanjang PKP 2.0.
Lian, S. J. (2020). Crises and Policy: COVID-19 Truly is Different.
Ong, K. M., Paulus, F., & Singh, J. (2021). Continued and Targeted Economic Assistance.
Saari, M. Y., Rahman, M. D., Utit, C., Zahuri, Z. A., Mokhyi, M., Sinjus, H. A., Halim, M. R., & Ahmad Kamal, M. K. (n.d.). Quarterly Labour Market Perspectives: Modest Labour Market Recovery
Sazali, N. T. (2020).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 - Time to Reimagine Social Protection.
Sazali, N. T., & Hamid, H. A. (2020). Bekerja Sendiri, Risiko Sendiri.
每月12.50令吉
- 无限畅读全站內容
- 参与评论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 与亲友分享《当今大马》付费内容
- 可扣税

 陈明忠
陈明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