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的日记书写:《安妮日记》丶《黑日》丶《方方日记》(下)
续前:危机时刻的日记书写:《安妮日记》丶《黑日》丶《方方日记》(上)
郁闷中的呼吸阀:《方方日记》的记忆封存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二〇二〇年二月二日)
作为一部无法正式出版的作品,《方方日记》的流传速度及争议,都比上述两部日记来得更快更多。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新冠病毒疫情恶化,中国政府决定封锁武汉市。
定居其中的方方,一方面接受《收获》杂志邀稿写“封城记”,一方面想记录个人生活和感受,在同月二十五日,在新浪微博开始每日一记,停笔于三月二十五日。至于《方方日记》则是读者後来命名,她觉得一日一记形式也属于日记,因此没有异议。
《方方日记》浅显直白,往往陈述所见所闻,并通过各种媒体平台广为转发,获得不少共鸣。方方平铺直叙的语言包含对灾难的怜悯,直率的言辞也常常有“警语”,比如她陈述“灾难是什么”: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六日: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小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灾难是你拖着病体在寒风冷雨中四处奔走,试图寻得一张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却找不到;灾难是你从清早在医院排队挂号,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还没有排到,你就轰然倒地;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断气;灾难是重症病人送进医院,如果他死了,进医院的时刻就是跟家人诀别的时刻,彼此都永无相见之日。
方方认为戴口罩丶不出门丶行动管制并无法完全概括这场危机。相较个人活动受限,文中一连串排比,才让灾难形象变得具体真实,因此触目惊心。这段文字还原混乱和悲痛的历史现场,当中最强烈的反差,就是个体的生对比群众的死。
死亡证明单丶运尸袋丶挤不下的病床丶排不到期的挂号丶来不及拯救的性命……方方突显了疫情底下激增的死亡人数,以及无法适时获得急救的无奈和哀痛。危机时刻,众人早已惴惴不安,这些文字自然令人更加难受,然而方方在同一天的日记已经坦言,“岁月在灾难中没有静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亲属的胆肝寸断,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
封城初期,疫情资讯模糊,众人惊慌失措,《方方日记》提供即时消息,针砭时事,成为许多人寻求慰藉的暂时出口,也成为各方人马的攻击对象。不少人抨击方方道听途说丶制造恐慌丶批评政权丶没有传播正能量。面对虚虚实实的谩骂,方方继续坚持一日一记,并且在文章里频频反击各种指控。她非常清楚,自己回应的不是单纯的事实真伪争辩,而是需要面对被意识形态笼罩的写作氛围。
方方在同年三月十九日的日记提到,多年前上大学,经常会讨论一些文学话题,总概为“老三篇”:“歌颂与暴露问题,喜剧与悲剧问题,光明与黑暗问题。”後来方方毕业丶工作丶成为职业作家,经过不少历史事件之後,让她发现,“别说我们当时的同学,就连整个文学界,在这些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你都可以写。重要的是你写得好不好。”
令方方感慨的是,几十年之後,这些问题似乎回到原点,因为方方被诘问的不是写作问题,而是被指责在灾难中,没有歌颂丶没有写喜剧丶没有写光明面。方方强调写作个体的定位和反思:
二〇二〇二月十七日:我是一个个体写作者,我只有小的视角。我能关注到能体会到的,只有身边一些碎事,以及一个个具体的人。所以,我只能作一点琐事记录,写一点即时感想,为自己留下一份存活过程的纪念……小说经常是与落伍者丶孤独者丶寂寞者相濡以沫的。与之携手共行,甚至俯身助人。
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以前谈小说时,我说,文学虽然是一种个人表达,但无数的个人表达汇集一起,便是一个民族的表达;而无数个民族的表达汇集一起,那便是一整个时代的表达。同理,一个人的记录,微不足道,更不足概括全貌,但无数个人的记录,汇集一起,真相便会以全方位形态露出水面。
方方坚持“我手写我口”,认为文学写作虽然只能涵盖微小视角,也仅仅表达个人立场,然而这个勇于发声丶追问真相的姿态,已经表明文学写作重视人情,以及关注大环境。写作人坚持站在弱势那方,是对不公不义的抵抗。方方没有想要利用日记广传的优势掌握对于疫情的话语权。她其实更期望,其他人可以从各自角度说真话,记录当下所思所得,由此重构事实全貌。
在同年三月十二日的日记里,方方提到,读者都认为“方方日记是我们在郁闷中的一个呼吸阀”,这或许是方方不畏舆论压力,坚持写作的主要动力。疫情爆发,日常生活暂时停顿,步伐和节奏失序,所有人都与外界隔离,只能通过媒体接收大量不安的资讯。在压迫的环境里,一个人的发言,已经道出不少人的心声;一个人的思考,可能涵盖不少人的反省。《方方日记》可以说是武汉封城时期的一道窗,让墙内墙外的人们,拥有一个可以跟进信息,了解生活状态的管道。
至于网络“喷子”的谩骂和攻击,方方的回应则可以看出她对媒体生态和舆论环境的深刻批评。她冷静地说,就让那些叫骂和议论保留下来,让後人观察: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五日:你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些叫骂的人是谁,他们的头像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共同特点,他们来自什么吧或什么圈,他们共同关注的人是谁,他们经常转谁的微博,与谁互动,你可以像发现病毒的源头一样,发现感染源从哪开始,什么时间同步叫骂,什么人在背後鼓动丶教唆以及组织,他们曾经还叫骂过什么人,他们最推崇谁,最服从谁的指挥,以及他们语言出处从哪儿来,与谁的语气大体相同,还有语言在叫骂中的变化,诸如此类……网络有记忆,真好,而且这记忆很长久。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让我的微博留言成为一个观察点,可以留下这个时代鲜活的标本。
方方总结,她的日记都是琐碎事物和随想,多半留不下来;然而经过成百上千人的叫骂,她的日记却可以永存,随之保留的也包括文章底下的留言和抨击。《方方日记》以及伴随而生的谩骂和指责,将会一同接受时间的考验,被後世检验评价。虽然大部分评论者都匿名或化名,评论也有可能随时删去,然而通过截图转发丶他人文章回应丶日记里的反击等等,都让这些无名氏的噪音留底封存,成为方方所言“这个时代鲜活的标本”。
可以说《方方日记》已经超越日记写作,它与当下的媒体形式紧密结合,成为危机时刻的特殊文化现象。她的写作抵触了主流叙事和写作禁忌,因此掀起惊涛骇浪。然而在主流叙事之外提供其他观点,以及挑战写作禁忌的迷思,关注被隐蔽的人情世故,一直都是一名作家的任务和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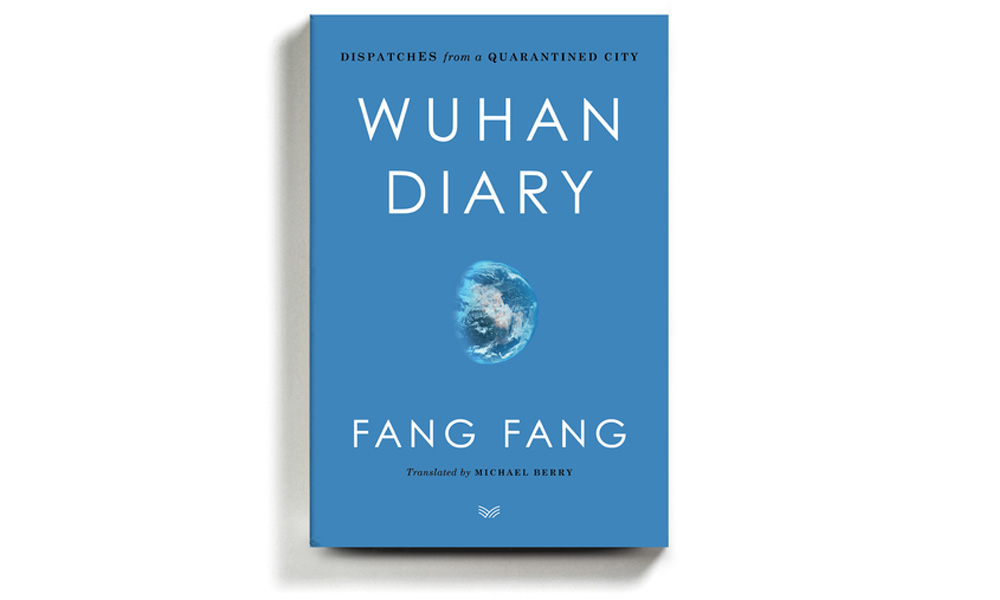
余论:“启示录”和“避雷针”
危机时刻,众人虽有想法和情绪,但不是每个人都掌握宣泄出口和表述能力。上述三位写作人都以敏锐的视角丶冷静的思考和精确的文字,在战乱丶政治动荡和瘟疫之时,梳理和面对种种杂念丶愤恨和恐惧。
这除了彰显写作人的现世关怀,也展示了回应危机的另一种途径。这些个体记忆和主观感受,除了让读者感受到鲜明的人心,复杂的时代背景,也构成危机时刻的个人史和生活史,甚至是後世管窥相关时代的微观记录。以史为鉴虽是老生常谈,然而处在危机时刻的人们,还是对这道理感受深刻。
比如说,白睿文(Michael Berry)即便遭受大量的无理谩骂和威胁恐吓,依旧坚持英译《方方日记》,因为他从日记里感受到深刻的人文力量。在瘟疫肆虐全球之前,白睿文发现《方方日记》已经溢出日记形式。
它的文字载体多元,包括微博丶微信丶电邮丶截图丶句子摘录以及pdf文件,而且文章往往附上各种留言丶批评丶链接丶图片丶视频等等,形成了一个多元复杂的文本组合。他在日记里读到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以及各种真实情绪和反思,决定即刻翻译,让日记得以广泛流传,也可作为观察现世的珍贵史料。
白睿文拿到方方一两个月之前的日记,就开始一周七天,每天超过十小时的翻译工作。因为翻译的时差,白睿文得以通过方方的经历和经验,预知疫情动向和生活变化。比如方方居住的武汉开始封城,众人不被允许群聚,强制性戴口罩时,白睿文生活的洛杉矶,人群还未有危机意识。直到疫情在美国肆虐,洛杉矶开始封城丶众人都受到行动管制丶开始呼吁群众戴口罩……方方日记所记载之事,又再上演。
这份“启示录”让他在美国仍旧漠视疫情之时,就在大学课堂上提起相关议题,适时取消群聚活动,甚至和家人讨论,是否提早让孩子在家学习。他坦言这场翻译计划最奇异的经验,就是自己渐渐模仿方方的生活模式。而翻译後记的一段话,除了是白睿文对恶意批评的回应,也可看做是危机时刻日记书写的意义:
If, as the trolls allege, Fang Fang’s Wuhan Diary is indeed to be “weaponized,” I hope it will be a weapon to show the power an individual possesses to cut through the noise and perhaps to effect real change. Wuhan Diary was the lightning rod and Fang Fang was the voice for Wuhan during its darkest hour; but in the West where is our lightning rod? Whose voice can we look to that will cut through the noise and demand truth and accountability? Against all odds, Fang Fang rose to the occasion...and so can we.
(如果真像网络“喷子”所断言,方方的《武汉日记》将被当作“武器”般使用,我希望它可以成为一个展现个体力量的“武器”,穿越舆论杂音,或许带来真正的变化。《武汉日记》成为那根避雷针,而方方也是武汉最黑暗时期的正义之声,但是在西方我们的避雷针又在哪里?我们又能期待哪一把声音能够穿越舆论杂音,替我们追讨真相和问责的权利?排除万难之下,方方已经挺身而出……而我们也行。)
李志勇,“业余者”成员。
编按:文内部分用词与本刊并不一致,例如文内称新冠病毒,本刊称为2019冠状病毒,为保留文章指涉的语境,本刊不做更动。
本文原收录于“业余者”小志03《疫中人》,段落略有调整。本文获得业余者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每月12.50令吉
- 无限畅读全站內容
- 参与评论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 与亲友分享《当今大马》付费内容
- 可扣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