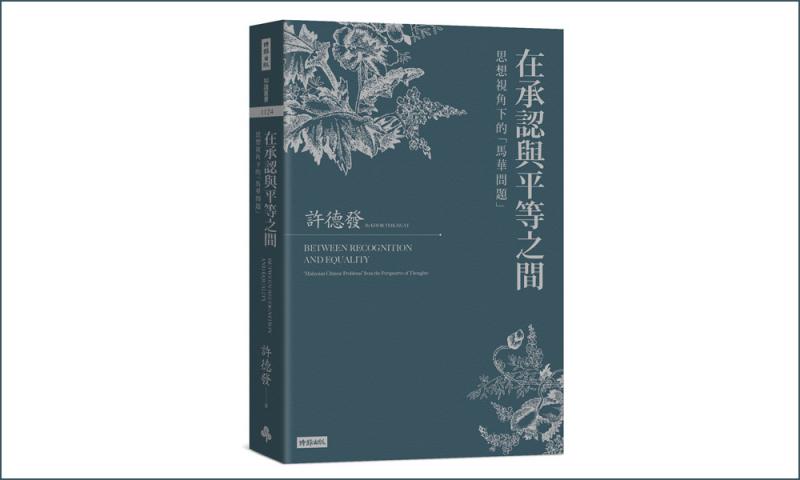“华人”问题与不/平等的政治:序《在承认与平等之间》
2018年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全国大选是个分水岭事件,自建国以来一直老树盘根的巫统严重分裂,三股在野的进步力量结成联盟,致使政治版图大幅重划,然而希望联盟执政不到两年后就被出卖,从而把大马国运抛入一个形形色色的极端种族主义四处飞飏的轨道。
马来西亚政治的发展今天已经坠入一个前所未见的新底点,就连一些长年深藏不露的温和的开明马来知识阶层人士也被迫伸出头来发出声音,人们甚至可以听到一、两个马来政治人物把马来西亚形容为“a failed state”。
把马来西亚推向这个境地的人,或者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我们称之为政客——或者是从政者或政治人物。在一九五○年代中,我这一辈青年学子读到当年(也是当地)的文化启蒙者连士升先生告诉他的读者:政客不可为!政客是负面人物!我依稀记得他把作为政治人物的人格/行为标准定得很高,几近于古书里所形容的圣贤或君子。
执政集团形塑既得利益群体
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对西方(欧洲)的政治传统(暨其与西方〔欧美〕现世的政治型态之比较)做了哲学兼历史的考察,她著重指出在古罗马城邦政治里,从政本然意味著义务,而执政遂意味著权贵地位以义务为天职(noblesse oblige)。这个权贵意涵在于义务的原则,可以在神州大地农村社会的民间秩序里见到,当然这是在儒家思想的天幕下自然生发,绅农门第建宗祠和藏书馆、办社塾、施医赠药、为乡党排难解纷,不一而足。
在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全面改造下,名义上的民主政治体制(nominal democracy)也带出了一类特殊人物:政客/从政者,以及他们的组织——政党。巫统建党之初,组党人之中有几人会意识到这组织将会发展成一个独立国度的现代型态的执政党——他们之中有些人是某个马来王室的权贵,也有些绅农型人物,有些人在跟英殖民当局的官员交往中受到政治启蒙,以及小学教员之类的初级知识阶层。
创党十年之后,这些人转型成为一个新独立国家的掌权人,再过二十年,他们以及后来的追随者们就蜕变成为一个牢固执政集团的既得利益群体,随著时间的推移,它和他们也日益僵化和腐化,国家机器变成私人利益输送的渠道,三权分立的制度沦为虚文,权力没有受到正当的监督和制约,治理机关从服务型恶质化为近乎专制的管制型政府,制度极度缺乏纠错的空隙和自我修复能力,制度及其具体操作缺乏确定性,致使民心涣散,国运日衰。
不言而喻的,经典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理性在全球经贸一体化和本国的内部利益勾兑的交叉作用下,腐化为一种只能说是弱肉强食型经济(predatorial economy),以及它赖以滋长并对之交叉滋养的金牛犊崇拜社会文化,市场上人人绝对的拜金主义,对财富和权力的绝对崇拜,也只有在这种鄙劣的社会文化底下,我们才能看到一个被控告偷窃数以亿计国家资财并已定罪的政府首长到处招摇,并且受到民众报以“我的领袖”(Bossku)的欢呼。
两年前希望联盟政府倒台之后,马来西亚政治就落入一种西班牙画家戈雅(Francisco Goya)所说的“当理性入睡之后,恶魔四处飞窜”的可悲境地。两年来国人不断听到种族和宗教极端份子此起彼伏的叫嚣,潜伏在体制内不同阶层的皂吏甚至嚣张地使用公权力、司法体制、宪法等手段,挑战立国之初早已规定的规范多元种族关系的宪制性安排,细如Timah(马来文,意为锡)牌威士忌酒受攻击刁难,钜如国内非马来族母语学校的合法性受到司法挑战,委实令人痛心疾首。
今天国家的领导层基本上是一种盲人下棋的型态,掌权的嘴脸们不懂国家治理(governance)为何物,连他们用冠冕堂皇的智囊机构去豢养的摩登博士师爷们也拿不出什么亮眼的宏大论述(grand narrative)来蒙骗底层蚁民了,来来去去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滥口号打转。极端种族主义姿态和排他论述是如此猖獗,就连老成持重的伊斯兰宗教学家、中庸的退休外交官以及过去操过某种权柄的前部长都感觉不能不出声批驳。
马来权贵集团的驭民术
极端种族主义政客集团何以能这么长久地操控政治权力呢?一言以蔽之, 那“论述”就是所谓的马来人至上原则(Malay Supremacy)及其旗下所推行的施政议程(Malay Agenda),这套论述长久以来既俘虏了基层马来民众,特别是乡村和园丘的农民(半岛的国会选区结构的比例形势基本上是“乡村包围城市”),甚至城镇的低收入阶层和小知识群体也受其蛊惑难解。
1969年大选后爆发种族冲突,嗣后推出“新经济政策”,在分配正义的名义下大规模推行扶助马来族经济力量的各种行政计划;这政策原定只实施二十年,然而至今仍没有结束。今天已经有马来人物发出呼声,主张结束给予马来人特别保护和扶持的新经济政策,那是马来人经济学界的老行尊。
还有马来政治界的后起之秀也在说,马来人在经济领域受到优待,最终不过是害到马来族本身。如果我们翻查旧资料就会发现,近似这样的言论早在马哈迪第一段执政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在一个实行名义上的民主政体的多元国家里,经济利益的分配正义是不可或缺的,这是用来平衡经济原生态固有的有与无、多与少不均衡的纷争与缺陷,然而人工的行政纠谬手段不能粗暴地劫甲济乙,不能违背自由市场的正当规律,也不能忽视机会自由相辅相成的重要。
极端种族主义的马来权贵集团何以能长期操控政治权力而主宰著国家的治理议程呢?一位马来人政治新秀说破了一般既得利益集团同流人所不敢更不愿坦白的原因——实在是一个政治与经济操作上的小逻辑,那就是操弄在民主政治和族群均势的大棋盘上佔最大优势的马来群众/选民,特别是底下层劳苦人民,一则以大量大规模以扶贫为名的行政措施来收买乡村农耕人民(包括拓殖区小园主)(这就是在马来西亚政治语境里所俗称的“拐杖”),一则以丧失这些特权/优惠为利器来威慑马来选民。
个人自由与公民责任
当然在这整个铺天盖地的行政拢络底下,媒体(马来西亚媒体业大概是全世界极少数几乎完全由执政党拥有和操控的国家)和教育体系也就扮演了愚民的角色,使那广大的长久获得免费利益的低下阶层民众不愿意离开那拐杖所赐予的舒服区(comfort zone),而变成上世纪一位从苏联“铁幕”里流亡出来的诗人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所说的“被俘虏/禁锢的心灵”(captive mind)。
人们常说:人人向往自由,自由可贵,其实在真实的世界里这格言隽语并不实用,在今天这个复杂而黑白不分的世界里,自由意味著责任,对自己负责,对个人的生活负责,更对自己的良心负责,而这是极其可怕的一件事:对自己负责,而天底下却有难以计数的心灵是没有内在能力和外在条件对自己负责任的,这就是那二战时期流亡到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心理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所说的“逃离自由”:别给我自由,自由可怕!
是的,我们何以会有如许多脑残政客盘踞在国家机器的内内外外,把国家不断推向“滥货国家”(pariah state)的深渊?简单的答覆是:“不是你们这些蠢货投票选我们出来捧上政权宝座的吗?”当然我们是应该去追寻一个更全面的答案的。这使我想起《圣经》里的一则寓言:薅稗子的权柄。(在这里我是抄书,一部圣书,但我得声明我不是基督教徒,我坚持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一个Christopher Hitchens / Richard Dawkin派无神论者,至少是一个朴素的神灭论者,一个在日常生活里也喜欢随缘进出佛堂、神庙、基督教堂、兴都庙堂等圣地的无神论者。)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说:耶稣设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了。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田主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田主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著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著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是的,坏稗子在适当时机要薅出去,好的麦子则要收在仓里。这就是所谓的权柄,就是选民善用手中的选票,知道何者为稗子,何者为麦子,并把稗子薅出去,除此我们别无其他通往天国的门票。
族群政治与平等之理想
三年前当新上台的希望联盟政府准备启动立法程序,让马来西亚向全球百余个联合国会员看齐,签署“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之国际条约(ICERD)”时,立刻引发巫统的强烈反对,属于希盟执政集团一员的土著团结党也加入反对的行列——尽管签署此条约本是希盟竞选宣言中的一个信条。这些马来政党当然以马来人社会代言人自居,就是因为马来人社会大多数都是常年处在米沃什所形容的精神境地,少数清醒的人也不想做出头鸟。
清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难道不是一条普世价值吗?马来民众不是也能受到这个条约的保护吗?其实这些都不成问题,巫统和土著团结党人所不能解开的一个死结是马来社会历来所享受到的特权和优惠将如何可以和此条约所主张的基本主张和信条并行不悖。
马来亚/马来西亚立国之初,在前殖民地主子英国的斟酌之下,就承认马来人是这个新国家的定义性族群(definitive race);由此衍伸的特别条件就是规定马来语文为国家语文,马来人普遍信仰的宗教(清真教)为官方宗教,而公民地位则采取兼容的政策,即对马来族是采血缘法则(Jus Sanguinis),而对非马来人如华人、印度人这些侨居客则采取土生法则(Jus Soli),即土生华印人可申请成为公民。这个兼容原则符合了马来亚一位建国思想先行者陈祯禄在一九三○年代以及在日据时期他在印度避难时所鼓吹的原则。
这几条立国时规定的特权都载入了宪法里,所以没有什么可以争论,其他嗣后在巫统长久执政期间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如新经济政策后期乖离原初精神,马哈迪以强人优势推行的朋党主义措施,以及国家与民争利的现象,都在种族均势上出现分配的偏差,则是要令人诟病的。这些措施都是以保护土著、为土著提供优惠的大论述作为宣传幌子,也就变成了政治禁忌,马来政党不愿去碰,非马来人政党或多元种族政党也不敢冒险去碰,以免闯到地雷。
那么像消除种族歧视公约这样一条主张普世价值的国际公约是否(不是应该或不应该)可能在国会通过呢?朝野政党其实可以尝试斟酌提出一条附加条款(rider),规定那些既有的土著特权和优惠/扶持措施(在国会决定要废除之前)不受此条约所影响,然而没有任何政党愿意踏出这一步,因为政客们都不愿在这个敏感而棘手的课题上付出任何沟通、交流与斟盘的些许政治成本。
人人生而平等,这是一种何其可贵的理想,然而事实上普天之下人人生来就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最显著的是表现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差距上,诸如经济生活的贫富不均以及相随的机会落差上。
美国数十年来实行的平权政策就是旨在男性与女性以及白人与黑人/有色人种社群之间弥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所原生的机会不平等弊病;这里所谓原生意指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之下私有财产制度所规定的内在条件。当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言,原生的弊病并非不可改革和修理的,而这也不仅仅是做制度修补师傅的工作,而是从根本上纠正制度的原生瑕疵,避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现象。
此外,近年来一些社会思想家也注意到不平等的现象不仅如此,原本立意良好的优则(Meritocracy)法则和制度,即在社会上推行选拔优秀人材的制度不意造成机会自由和分配正义都沦为空谈,使平等更加遥不可及。
“分配和机会”的二元困境
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一直都在对分配和机会这个虽二而一的政策困境感到揪心,这问题甚且影响到很多人的安身立命的考虑。大多数华人并不介意,甚至相当认可政府采取平权政策来扶助和提携在经济条件和生产技能上较落后的马来人,诸如乡村农户和园丘小园主,甚至经济条件是城市里的低薪阶层,然而历届政府的平权政策实在是声东击西,扶助并不到位,常常大撒币都是为了买选票和支持,更是在施政制度上制造建国初年都闻所未闻的种种问题。
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朋党作风,最早是在国家企业私营化运动之下,把大量国家财富私相授受的输送给朋友、亲戚和政治支持者,基础建设项目、官营公司、发展项目等等,就是如此这般像肉包打狗似的落入有关系的人手中,制造了马来西亚社会过往从未见识过的在品德和识见上都不符地位的种族权贵阶层。
另外,历任首相无一例外的运用特权把官联公司(通常都是垄断企业)的高管职位当做政治礼物般赏赐给政治附庸,诸如选举落败的部长,或执政党内烂泥般扶不上壁的死忠支持者,给大马政治带进了恶劣的“旋转门”(political revolving door)现象,另一方面把呆滞的血液注射入原可发挥创造力的企业肌体内。
我个人最不愿见到的现象,则是如此这般胡搞,社会上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特别是一线城市内各族市民中的贫民阶层低端人口,很多人都是基本生存条件都说不上。一方面过去半个世纪随著经济发展的需求而造成国内境内移民(interior immigrants)大量增加,乡区居民大量涌入城市,另一边厢历届国阵政府厉行压制工人运动,不允许新兴企业组织全国性职工会,与此同时又压低最低工资水平,直至最近三、两年才稍微松绑。
凡此种种恶劣措施使得城市贫民生活苦不堪言,很多人都得靠两份工作来维持基本生活、子女教育、医疗、养老、单亲母亲福利等等,其他需求就得仰赖政府的“手杖”施舍,很多马来贫民就如此这般成为执政党的政治禁脔。
历史沉迹中剖肌析理
许博士这部巨制让我写序,写了上面那些霉气十足的话,实在是佛头著粪,自己都觉得很难为情,无奈我这傢伙就是积习难改,自己给人写序,从来就是服膺知堂老人所说的“以不切题为旨”的作序章法,反正我一身野狐味,实在没有学力摸索学术这门庙堂功夫,只能找个旁门左道遁逸而去。
许博士从青少年时期就关注马来西亚华人问题,出道后更长期研究思索,冀为这个问题梳理出个明晰的脉络,这无疑是项艰钜的思想工作;所谓马来西亚华人问题,既是在国家实际政治中不断摆荡变化的问题,更是在历史的嬗替中基本上已经定格的问题,前贤的足迹似真似幻有如摸象,要描述出个全豹殊非易易,而许博士却能将之作为长年治学的关注对象,每能在纷繁的历史沉迹中剖肌析理,洞见症结,实为难能可贵。
我与德发相识近三十年,当年在华研《资料与研究》的编辑会议初识,后来更在华研共事,常有机会共餐聚谈,其间最亲切的经验莫过于共同编辑《人文杂志》,定期前往“永远的文艺青年”庄若住家监督排版工作直至深夜。
青年学人德发很早就透露出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生命取向,我还记得他说的治学范围是思想史领域,透露出他秉性深远的终极关怀,而他嗣后的生命轨迹也确实是循这条路径前进。德发秉赋耿直敦厚而朴素,在这个流光溢彩、钱权横流的时世,他是个处士型的现代学人。
2022年6月吉隆坡
张景云,2007年退休前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历任《新通报》、《南洋商报》、《东方日报》总主笔。曾受聘为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人文杂志》主编。参与创办中文评论网站《燧火评论》。2010年膺佛光山星云大师新闻传播大奖(大马区)。著有《言筌集》、《见素小品》、《云无心,水长东》、《犬耳零笺》、《反刍烟霞》、《炎方丛脞:东南亚历史随笔》等书。编著《马来西亚建国三十五年华裔美术史料》、《当代马华文存》、《威北华文艺创作集》等。
编按:本文原为许德发《在承认与平等之间: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一书之序言,文章标题与小标为原文所无,均为本刊所加。
本文段落有所调整,以方便网络阅读,文内思想家名字中英文顺序与译名有调整与补充,一处学派名称按惯用之译名,部分政党、宗教名称按本刊惯用格式,其余没有更动。本文获得台湾时报出版社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本刊近日也将刊发该书之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序文,敬请垂注。
该书之导论,请点击许德发〈华人之为“问题”:危机溯源与时代精神迭变〉(原题〈“马华”作为问题与研究的态度〉)。
欲知该书详情,敬请点击此书介。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每月12.50令吉
- 无限畅读全站內容
- 参与评论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 与亲友分享《当今大马》付费内容
- 可扣税